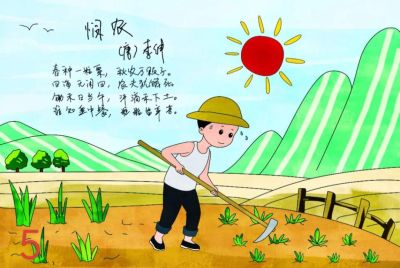? 韩祝贤文
七月中旬,正值夏收夏种的繁忙时节。这时的太阳炽热得有些“毒辣”,农民们都称它为“毒日头”。天空湛蓝如宝石,万里无云,那似火球般熊熊燃烧的烈日,仿佛离人们格外近了,将气温一下子飙升到近四十度。屋上的瓦片、道上的石板都被晒得滚烫,村子里房前屋后稀稀落落的几棵苦楝树上,蝉儿们占据着栖息之所,还不知趣地“知啊!知啊!”叫个不停。被热浪包围的人们,本來就暑热难耐,再被这蝉声一搅和,浑身更是燥热无比,整个世界仿佛只需一根火柴划过,便能燃起熊熊大火。夏天的东风极为珍贵,难得一遇,偶尔有一两阵微风轻轻拂过,让汗流夹背的人们,仿佛吃到了冰棍一般,享受到一丝难得的凉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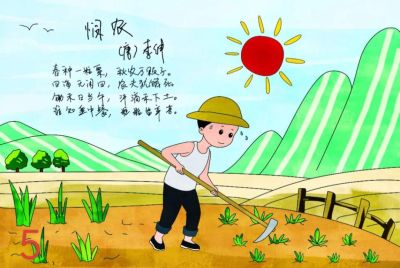
此前梅雨季时,江河里水是丰盈的,然而,由于烈日下新苗田大量灌溉用水,河水以每日下降半尺的速度迅速干涸。原本的村河此时已变成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,两岸的人们甚至可以挽起裤腿,不湿膝盖就淌水过河。人们不禁担忧起农田灌溉、生活用水,乃至田头地角蔬菜的生长,可旱情依旧在持续。


午后两点,生产队长抬头望一望天空,心中思忖着是否该出工下田了。尽管午后依旧酷热难耐,但“双抢”的进度迫在眉睫。他咬咬牙,吹响了出工的哨子。那些在弄堂口、竹林旁阴凉处歇着的农民们,纷纷提起茶甏,扛起铁耙,聚集到路口,朝着耕作的田头走去,只是他们的脚步显得疲惫。昨晚收割完的稻田,夜里灌好了水,天还未亮时,他们就摸黑起来,开了两个多小时的早工才翻整好土地。上午一直劳作到十二点才回家吃午饭,已整整工作了八个小时。家中佐歺以饭焐茄子青南瓜,丝瓜葫芦干菜湯,一碗乌干菜是常和饭。若能买來供销社支援双夏的物资: 一角钱五块的醉方霉豆腐,二角钱一斤的龙头鱼鲓,那绝对是算有现钱人家的美味佳肴了。连日的高强度劳动,已经有人中暑,颈背上捏出了满满的紫黑色痧痕。“双抢”这场硬仗,即便不想打也得打,即便承受不住也得挺住,他们没有退路,也毫无怨言可诉处。


住在集镇上的公社主任,患有气管炎,身形又黑又瘦,一动就气喘。他每天都要步行三里多路,来到村中大队,蹲点指导“双抢”工作。他早上来,中午回去吃饭,下午再来,傍晚才回家,有时晚上还要参加大队召集的小队长会议,开会研究“双夏”进度,不得不再次赶来。烈日之下,他头戴一顶小草帽,脚趿一双塑料鞋,仅带一条擦汗的毛巾,就这样步行往返,与农民们同甘共苦,奋战在“双夏”第一线。


六七十年代盛夏的天气,一是酷热难耐,二是傍晚雷阵雨频繁。常有连续十多天高温,但有时下午会来一场短暂的雷电交加、狂风大作、雨如倾盆的大雷雨。这可着实苦了负责晒场的妇女们。
每当下午三点过后,西南角那片湛蓝的天幕上,会缓缓升起一团团状如棉絮的白云,太阳渐渐隐去,云团显得格外洁白透亮。而后,云团越变越大,慢慢转黑,隐隐传来低沉的雷声和闪烁的电光。农谚有云:“南闪火门开,北闪有雨来。”这来自两个方向的雷阵雨前奏,往往预示着雷雨真的会到来。云层越积越厚,电闪越来越烈,几阵狂风刮过,大雷雨便真的来了。它的到来能让气温下降,人们晚上得以睡个好觉,恢复些许体力;也能缓解一些旱情,让贵如油的雨水滋润庄稼,农民们满心期盼着它的降临!然而,这却让晒场上的农妇们犯了难。经验丰富的妇女队长一察觉到天气变化,立刻下决定,要赶在雷阵雨到来之前,将摊在晒场上晾晒的稻谷迅速收纳进仓,以免被雨淋湿而发芽。刹那间,晒场仿佛变成了战场,妇女们有的用木耙推,有的用畚斗装,有的用箩筐抬,呼喊声此起彼伏:“快些!快些!大阵头就要来了!”短短十多分钟,就将稻谷安全入库。尽管她们浑身大汗淋漓,衣服湿透,头发上沾满了草屑,累得腰酸背痛,但看到稻谷安然无恙地进了仓,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


晚上九点过后,村河上的每座石桥上都坐满了纳凉的人,清一色是些光着膀子的爷们。他们手持蒲扇,一边摇着扇风,一边天南海北地闲聊,从“双抢”的进度,聊到电影《沙家浜》里的阿庆嫂和刁德一,甚至天马行空地聊到姜太公直钩子钓鱼。此刻的他们,才算是最放松的一刻。乘凉一直持续到子夜临近才结束,纷纷回到那个或许三代同堂、人禽混居的小瓦平屋,小孩已经入睡,床边笼中的鸡鹅也安静了,室内的热气消散了一半。他们可以勉强安睡上四、五个小时,去迎候与今天一样繁忙而辛苦的明天。


那时的农民兄弟真辛苦。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,农民就是这般辛苦,这是农民们辛勤劳作的真实写照。如今我们享受着幸福生活,绝不能忘却前辈的农民,我们的父老乡亲曾经所付出的艰辛。
2025--08